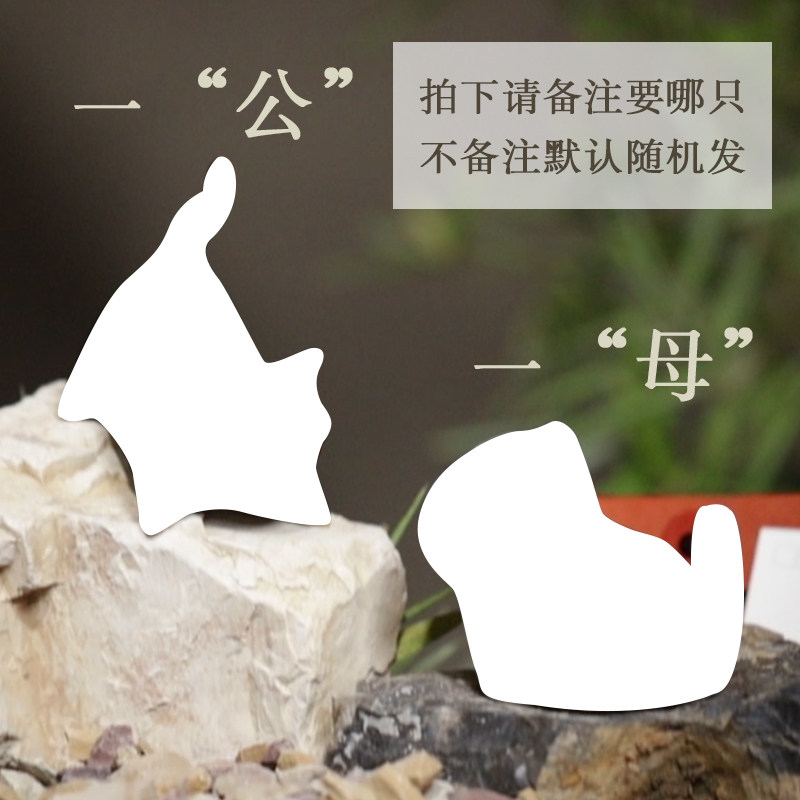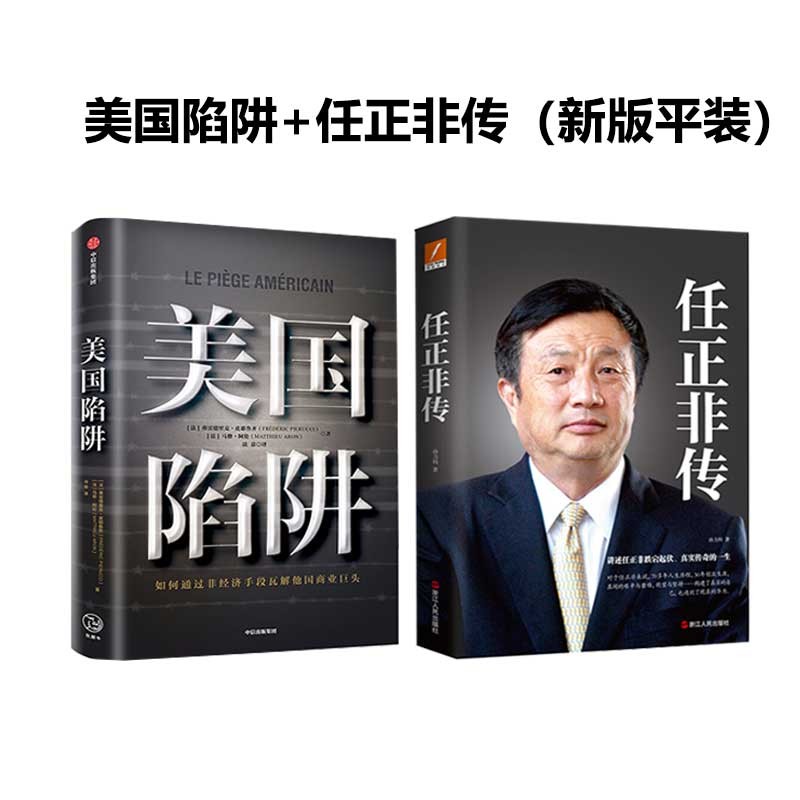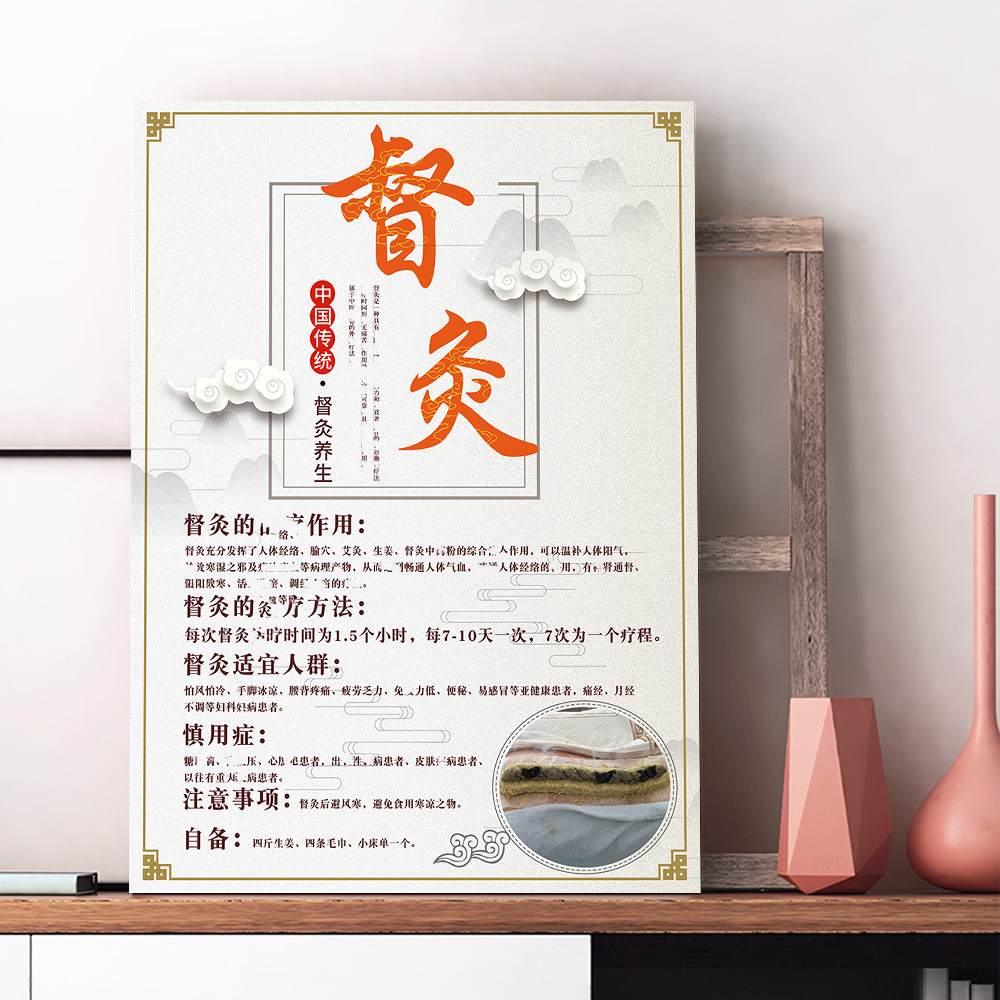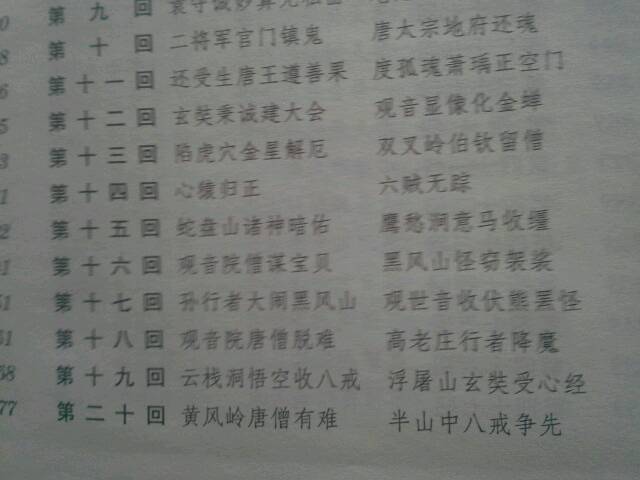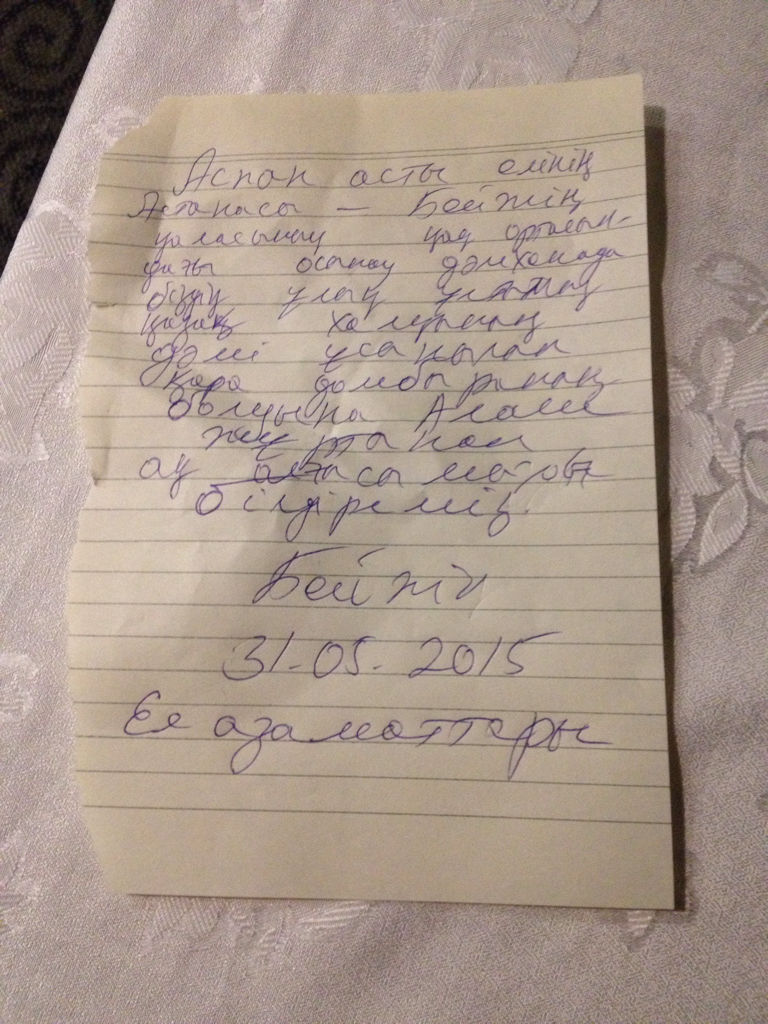一、吴又可是怎么创始温病学?
吴又可(1582—1652),名有性,字又可,号淡斋 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温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以医为业,是明末具有创新精神的著名医家。
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温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以医为业,是明末具有创新精神的著名医家。
温疫,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讲的传染病,它对人类的危害性极强,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瘟疫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
明末清初,连年战争,灾荒不断,各种传染病不断流行。吴又可59岁那年(1641),江苏、河北、山东、浙江等省,温疫流行甚剧,他的家乡吴县一带也不例外。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者。”当时医家按经典方法治疗,多不见效,死亡颇多。吴又可沉痛而深刻地批判医界泥古不化的害人思想说:“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遵守古代的医法,不切合今天的病情,把今天的疾病去同古代医书对号,根本得不出明确的论断,所以,这样开方给药就不见效。)病愈急,药愈乱。这“干村辟历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凄凉景象,使他感慨不已,愤然冲破习惯势力的桎梏,废弃仕途,不应科举,走上了研究医学的道路。他遇到的当务之急是“流行病”。他刻苦钻研前人及民间有关传染病的治疗经验。不怕传染,不辞辛苦地在病区、病家为患者诊治疫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和临床实践,他渐渐体会到以仲景之伤寒学说来论治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与愿违,遂产生了另创新路,以提高疗效的想法。他推究病源,创立“戾气”说,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一套温热病的论治方案,提高了疗效。他将这些经验经过整理著成《温疫论》一书。《温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又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为温病学说的创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吴氏认为:瘟疫病的发生,既不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因为外感邪气,而是人体感染了一种“戾气”。他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是天地间一种戾气所感。同时还特别强调提出这种戾气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物质的一种形式。”他说:“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肯定了气即是物,物即是气。他反对厚古薄今,墨守古法的医疗作风,在他的医疗著作里指出:“守古法,不合今病。”在这种注重实学观点指导下,吴氏潜心研究温病之病因、病证和传播径路,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温病都是感受一种“戾气”,而是许多种。所以又称之为“杂气”。他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明确区分了伤寒与温病在病因上的不同,他说“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温病感天地之戾气”。同时指出戾气是可以防治的。吴又可关于瘟疫病病因的认识,最接近现代的微生物致病学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关于疫有九传的论述和对瘟疫病症候的详细观察,说明他充分认识到外感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使用达原饮力图直捣膜原、驱邪外出的治疗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人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吴又可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而是香致病,既与戾气的量、毒力大小有关,也与人体抵抗力强弱有关,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突破了前人关于“外邪伤人皆从皮毛而入”的笼统观点。吴又可的勇气,鼓舞了清代的温病学家,他们不仅吸取了外感邪气“从口鼻而入”的观点,而且也大胆地提出了外感热病的不同传变规律的新学说,终于建立起与六经不同的另外的辨证体系,丰富了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
吴又可还提出,瘟疫病有强烈的传染性,不论是年老体迈的老人还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很容易感染瘟疫。并且在人和动物之间有着同等的机会感染瘟疫,有些瘟疫病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来回的传播。导致这些瘟疫的戾气也是不同的,不同的戾气导致的瘟疫的临床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吴又可毕生从事医学,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有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同时吴又可还往往是出奇制胜。相传有一天,来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被认为是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氏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温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是吴又可惟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50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30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
二、吴又可的“杂气说”是什么内容?
自从人类开始定居,瘟疫就如同附骨之疽不断纠缠人类,而且越是人口众多、越是文明发达的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和频率也就越高。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跟瘟疫周旋了数千年,产生了一大批关于瘟疫的观点和理论,尤其以明末的吴又可提出的“杂气说”为集大成者。
吴又可的“杂气说”,早在微生物学出现之前,就大胆地提出了传染病来自人体之外的“杂气”,而人之间会因为“杂气”的交换,通过口鼻患病,实事求是地说,吴又可的理论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思想贡献。
中国古代的“疫”与“瘟”
中国古代将传染病称为“瘟疫”,从词源发展上说,先有“疫”,后有“瘟”。
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无“疫”字,这并不表示商周之际没有大规模的传染病,当时因为人口较少,且爆发次数较少,所以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并不深刻。到了战国时期,人口增加,传染病开始大规模流行,于是在《墨子·兼爱下》中就出现了“疫”字:“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
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也在《月令》篇中提到了“疫”:“行秋令,则民大疫。”东汉时期,由于传染病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于是《说文》中专门解释了“疫”——“疫,民皆疾也。”
《说文》中有“疫”,但没有“瘟”,是因为“疫”字就可以笼统指称传染病了,而到了东汉末年,刘熙所著的《释名》中出现了“注病”,所谓“注病”,即“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显然就是指急性传染病。
急性传染病的流行,使得“疫”字无法概括所有传染病的形式,于是“瘟”字就出现了,成书于东晋的《抱朴子·内篇微旨》记载“经瘟疫则不畏”。也就是从这时起,古人称传染病为“温病”,“温”与“瘟”其实是一个字。“温病”的意思有两个:一是指发病原因——“温气”外侵;二是指患病症状——身体发热。
从词源来分析,“疫”侧重传染病流行的特点,而“瘟”强调人因“温气”外侵而患病,且具有发热体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瘟疫就是由外力作用引起的,身体发热的传染病,可以说中国的瘟疫概念基本上总结了传染病的特点。
中国古代对瘟疫的研究
秦汉至宋元时期
秦汉之际,中国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因此瘟疫也开始频繁出现。
成书于秦汉的《黄帝内经》专门研究了“疫病”,书中指出“疫”的共同特征:“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另外,《素问》篇判断了“疫”的爆发原因是天气——“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虽然秦汉时期人们对瘟疫多有研究,但仍然无法制止这种传染病的流行,比如王充在《论衡·命义》中说“温气疠疫,千户灭门”。曹植也在《说疫气》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爆发的一场大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户而殪,或覆族而丧。”
由于瘟疫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古人对传染病十分恐惧,所以对待瘟疫的态度十分决绝,比如在《大戴礼记》中,古人提出的“休妻”的“七出”中,就有妻子患“恶疾”一项,这种“恶疾”并非一般疾病,而是有传染性的疫病。因为害怕传染众人,无法参与家族祭祀,所以才规定有“恶疾”的妻子可以休掉。
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御览》是一部百科全书,在《养生要术》篇中,就记载了古人防治“瘟疫”的一种方法:腊夜持椒卧井傍,勿与人言,投于井中,除瘟疫。
明清时期
明清两代由于玉米、马铃薯和番薯等高产量粮食作物的传入,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与之相应的是瘟疫也频繁爆发。据统计,有明一代276年间,共发生大规模传染病64次,而清代国祚295年,瘟疫出现了74次。比如道光年间爆发的一场瘟疫,据汪期莲《瘟疫汇编》记载,当时“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死亡者。”
明清之际,由于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很多人聚集在村镇和城市,瘟疫一旦出现,必然造成巨大的损失,于是中国人在结合古代医学典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著作的基础上,通过防治瘟疫的实践,逐渐形成了“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在明清交替之际成形,明末医生吴又可的《温疫论》既是“温病学说”的理论源泉,也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治疗传染病的专著,对医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吴又可与“杂气说”
吴又可,原名吴有性,字又可。他生活于明朝末年,当时正是瘟疫频繁爆发的时期,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华中和华东地区疫病爆发,吴又可深入疫区,通过在一线接触和治疗瘟疫,获得了大量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完成了《温疫论》一书。《温疫论》首先思考了传染病的起源,吴又可认为“杂气”是造成瘟疫的罪魁祸首。
“杂气”说
吴又可否定了古代关于瘟疫的种种解释,尤其是《黄帝内经》判断瘟疫是“冬伤于寒、至春为温病”。他在《温疫论》一开始就提纲挈领地表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把这种“异气”叫做“杂气”,并撰写《杂气论》《原病》等专篇详加论述。
吴又可认为传染病有不同种类,不同等而视之,虽然患病原因都可称“杂气”,但杂气之中又分不同气,所以,某些病只传染特定动物而不传染于人,传染人的病也不一定传染动物。
他在《论气所伤不同》篇说:“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吴又可已经区分了传染源,跨出了防治瘟疫的一大步。
“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在这里,吴又可又总结了传染病的一般特征:患病各异,以传染为共同表现。然后,在“杂气说”的基础上,吴又可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传染病的理论。
第一、瘟疫来源
吴又可推翻了前人关于瘟疫跟季节有关的论断,提出了疫病的病因是“感天地之异气”,所谓“异气”,就是他发明的杂气,而杂气,就是充满了微生物的空气,在病毒学和细菌学出现之前,吴又可对瘟疫来源的认识是极为准确的。
第二、瘟疫传播途径
吴又可通过《温疫论》分析了瘟疫的传播途径,他认为瘟疫传播有两个途径,即“天受”及“传染”。所谓“天受”,是指看不见的空气传播疾病,而“传染”指的是病患与其他人的接触导致疾病传播。吴又可说“凡人口鼻通乎天气”,所以“邪自口鼻而入”,从这一点上看,他明确发现了病毒和细菌是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的。
第三、瘟疫防治方法
经过大量实践,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了许多防治瘟疫的方法,除了外力作用,他尤其重视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作用。吴又可认为“本气充满,邪不可入”:如果人体抵抗力强,即使接触传染源,也未必发病。这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总之,吴又可的“杂气说”,以及其著作《温疫论》将中国古代防控瘟疫的思想和理论提到了新高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瘟疫与历史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城市发展水平一直很高,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始终保持着大量人口,社会繁荣带来的一个负面作用,就是古代瘟疫的传播和蔓延。中国先民通过防治瘟疫,摸索出了一套朴素的医学理论,而明末吴又可的“杂气说”和《温疫论》,将这种朴素的医学理论系统化、理论化、专门化,是中国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便放在现代医学环境中,它们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三、哪本史书上有记载吴又可?
冉闵(rǎn mǐn)(约322年-352年) 冉闵(约生于西元322年左右,卒于西元352年6月1日),汉族,有文献记为“染闵”,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是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冉魏的君主。民族英雄,中华文明之保护者。冉为今人所广为人知的是屠杀胡人的命令,即杀胡令。他是拯救了汉族的抗胡英雄,以勇猛著称,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勇将之一。 这位将军异常英勇,正如晋史对他的描述“身高八尺,善谋略,勇力绝人,攻战无前”,每次临战冲锋在前,骑朱龙马(难得一见的千里马),他左手使双刃长矛(两头施刃,锋利无比的古代兵器),右手持连钩戟。其勇猛令五胡军队无人能挡,每战杀敌无数。闵左操双刃矛,右执钩戟,骑朱龙马,每战冲锋在前,杀敌数百人。 如《后赵录九石虎传》载:三个胡酋趁冉闵率大军进攻其它胡酋的机会,率骑七万袭击邺城,冉闵得知后,急率一千余骑兵回来救援,刚好与胡骑在邺城北面相遇,冉闵一马当先,所部千余骑都跟着奋勇冲杀。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 《十六国春秋》《甲府丹册》等载:凶奴刘显在冉闵攻襄国之后,帅众十万攻邺,闵率数千骑出战,冉闵大败刘显,斩万人,冉闵带军追杀,再战,斩三万余人。 《十六国春秋辑补》载:“冉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双刃矛也称两刃矛,“两头施刃”,锋利快捷,最为冉闵常用。 他在众胡联军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中创造了很多军事奇迹,与鲜卑的决战前,他以一万汉军敌鲜卑铁骑十四万鲜卑铁骑十战十捷。 中计被困的冉闵骑朱龙马,持矛戟,于十余万鲜卑铁骑军中,手刃三百余鲜卑强兵悍将,及至战马受伤(一说朱龙马是累死的)倒地被俘,面对鲜卑国主质问仍大呼:“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天下大乱,你们这些禽兽一样的蛮夷尚且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们堂堂中华英雄呢!) 死后被其对手追封为“武悼天王”,一个武,一个天王,入木三分地体现了胡人对其深深的畏惧 [编辑本段]英雄事迹 公元309年,乞活军活动在黎阳的一支在和匈奴前赵帝国的战斗中被打败,冉闵的祖父冉隆和叔父冉襄等亲人都殁于此役。冉氏家族留下一个11岁的少年——冉瞻(按现在的标准还是一个孩子),冉瞻带领所部乞活余部继续与胡人英勇战斗。 公元310年,石勒(此时是前赵的大将)攻打河内,勒见两军阵前的一少年英勇非凡,长而勇悍,精于骑射,阵前临矢石不顾。勒赞曰:“此儿壮健可嘉!”冉瞻寡不敌众,被俘。石勒徙冉瞻及其部众于兰陵郡。327年,冉瞻在和匈奴前赵的战斗中被斩于阵前。冉瞻之子就是后来的冉闵。冉闵除继承了父亲的勇猛外,还善于使用智谋。 公元316年,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虚弱不堪,最终被匈奴人灭国,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天下大乱之机入侵中原。 公元338年,少年冉闵首次参加战争,在昌黎大战,史载后赵诸军尽溃,唯游击将军冉闵三千汉军独全。此战后,冉闵成名,被石虎提拔为北中郎将,参加了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事(当时北方燕代之地,后赵境内有内迁的丁零,乌桓,夫余等各族各部,时常有叛乱,外有慕容鲜卑常发兵寇边)。冉闵在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斗中屡立奇功(其间也有两次调到外地作战)。 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一些胡族甚至从此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在返迁的路上这些不同民族的胡族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夺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诸胡乱中华时,北方汉人被屠杀的只留下四五百万,最主要的凶手是匈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这个民族有拿人头祭祀的习惯)冉闵灭羯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匈奴为主的胡兵。冉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羯族与匈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 公元350年冉闵率军于凌水河畔大败鲜卑燕军二十万。擒斩燕军七万余人,斩首上将以上三十余名,焚烧粮台二十万斛,夺鲜卑北燕郡县大小二十八城,冉闵威震中原。后冉闵推翻羯赵,称帝建国,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挟胜利之势,突袭各路胡军。先后经历六场恶战。 (1)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匈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匈奴首三万; (2)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 (3)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 (4)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 (5)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 (6)六战又有以步卒不足万人敌慕容鲜卑铁骑十四万不退反进竟十战十捷! 几番大战,打出了汉家铁骑的威风,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匈奴、羌、氐等胡人势力被迫撤出中原。石遵、石鉴、石琨、石宠、石蟠被灭三族,羯族的主力军被完全消灭。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石虎一生造孽无数,终于在子孙身上得到了报应。 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1万人马(步兵为主)去争粮。结果被鲜卑的14万大军(骑兵。还有数万后续部队)包围。在拼死突围的冉魏士兵掩护下,冉闵连杀三百余人,终于杀出包围圈(战斗经过本文从略),但那匹和冉闵一样勇猛的朱龙战马却因过度疲劳而倒下,冉闵被俘,他的手下仍然在机械地和敌人拼命,掩护随军的其他重要官员撤离战场,一直杀到最后一人……慕容恪捉到冉闵后,献与国主慕容俊,慕容俊嘲笑冉闵:“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呼!”慕容俊大怒,令人鞭之三百,然后送至龙城,斩于遏陉山。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正史记载,决非杜撰)作者语:冉闵壮志未酬,天地为之大恸,可惜上天既然体恤冉闵的用心,为何不干脆赐他胜利的结局。为何还要让他的冤屈千年不得昭雪,受尽同胞的谩骂。苍天不公,造物不仁,不知何时冉闵的英雄事迹才能在世间广为流传。 冉闵就义后,冉魏国的臣子绝望至极,悲天呼地。纷纷守节自缢,少部分逃往东晋,无一投降前燕者。冉魏几十万汉人不甘受辱,纷纷逃向江南,投奔东晋。东晋军未能及时接应,使得几十万百姓中途受到截击,死亡殆尽。晋将自杀谢罪。 由于冉闵的王朝时间很短。大臣多自杀殉国。没有人给冉闵写书立传。后来统治北方的北魏(鲜卑王朝)的史学家把冉闵大骂一顿。在史书上没有人为冉闵正义直言。而后代又缺乏资料,只能根据以前遗留的资料来整理。某些太监史学家片面强调冉闵的杀胡。而不说明冉闵杀胡的原因。想想冉闵一声令下,中原百姓和入塞胡寇无月不战,日日相攻。可见冉闵当时的政策是顺应民意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并不是冉闵有心挑拨。而是当时的民族矛盾不可调和。那些穿着兽皮。吃着生肉的野蛮部落。哪里懂得礼仪廉耻,生命的价值。入侵印度的蛮族部落把创造古代印度文明的当地人当作奴隶一样的驱使。印度的种姓制度大家都知道吧。21世纪的今天还生活在印度社会低层的贱民。就是那些几千年前被征服的印度本国人。冉闵天王昭告天下,邀四海豪杰奋起杀胡。屠胡令所到之地。中华子民纷纷响应。正因为冉闵,我族方才免于重蹈古印度人之悲剧。 冉闵被胡人收做义子,在南朝的史书从来没有记载。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被人篡改的史料来一窥这位1700年前英雄的丰功伟绩。冉闵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拯救了将被欧罗巴人种同化的中华文明。为我们这些后代夺回了生存空间。冉闵的武功决不亚于岳飞!岳飞其实是想成为第二个冉闵。冉闵的功绩与日月同辉!冉闵是英雄,关中80万汉族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跋涉来投奔冉闵就是明证。 生平事迹 永和五年(349年),石虎死,石世即位。同年五月,石遵得到冉闵支持发动政变推翻石世。起初,石遵答应立冉闵为皇储,後来却立石衍为皇储,引发冉闵的不满。孟准等人劝石遵诛杀冉闵,石遵便与其兄石鉴及母亲郑樱桃商议,郑樱桃认为石遵之所以能够即位,冉闵有功劳,不可杀他。会後,石鉴将此事密报冉闵。冉闵遂挟持汉族将领李农和王基推翻并诛杀郑樱桃与石遵,改立石鉴。冉闵被任命为大将军,并掌控大权。石鉴即位后,胡汉两族间的矛盾逐步走向激化,胡人不断掀起暴动和兵变.350年,石鉴欲杀冉闵,事败後反为冉闵和李农所杀。冉闵杀石鉴之前,发布了“杀胡令”和“讨胡檄文”致书各地,从面引爆了汉族人民积压了近半个世纪的国仇家恨,点燃了汉族人民的复仇反抗怒火,冉闵宣布:“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于是汉族人民对胡人进行空前规模的民族复仇,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史载当时的全国各地方的汉族人民“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头发略有发黄者亦被杀,前后约有二十万人被杀。其後建立魏国,依然建都于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城西南20公里邺城遗址,见图1),改年号永兴。冉闵遣使临江告东晋:“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由于冉闵已称帝,无法得到东晋支持。 冉闵的残酷屠杀引来胡人猛烈的反扑。350年,石虎庶子石祗于襄国(今河北邢台)称帝,胡人将官纷纷响应。350年1月,后赵汝阴王琨及张举、王朗率军七万伐冉闵,冉闵率骑兵千馀与战于城北,大破之,石琨等大败而去;350年6月,六月,石琨又率大军10万进据邯郸,后赵镇南将军刘国自繁阳会之,冉闵又率军大破之,死者万馀人,刘国还繁阳;八月,后赵张贺度、段勤、刘国、靳豚集中十余万主力于昌城,将攻冉闵,冉闵率军反击,战于苍亭,后赵军全军覆灭;351年,石祗联合鲜卑、羌人夹击冉闵,冉闵因屡胜而轻敌,导致大败,部众大量死亡。此战后,冉闵所据的徐州、豫州、兖州和洛阳归降东晋,东晋势力于是重返中国北方。冉闵继续与胡人攻战。期间冉闵诛杀齐王李农及其三子。351年,石祗部下刘显在阳平之战中为冉闵击败,被迫投降冉闵,并回军杀死石祗,从而后赵灭亡。不久刘显又背叛冉闵,自称皇帝.352年正月,冉闵率领8000骑兵攻克襄国,杀刘显,至此后赵残余势力基本被消灭.但前燕军攻势日急,前燕慕容恪率10万骑兵进攻冉闵,追至廉台(今河北石家庄东部无极县东北),起初冉闵出击,十战十胜。后来陷入鲜卑骑兵重围,冉闵突围东走二十馀里,坐骑朱龙突然死亡。冉闵於是被赶上的前燕兵所俘。前燕大军随即进围邺城,邺城守军艰苦抵抗鲜卑军达100多天,粮尽援绝,人相食,八月邺城陷落,冉魏灭亡。冉闵被送於蓟城(今天津市蓟县),前燕国王慕容俊企图乘机嘲笑冉闵,道:“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大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慕容俊恼羞成怒,令人鞭之三百,“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俊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岁永和八年也。”(肆行劳祀曰”悼“;年中早夭曰“悼”;恐惧从处曰“悼”,这里的“悼”,意指“年中早夭”,表示同情、悼念,“武”为美谥,意为武勇过人,演义小说《五胡录》则以为“武悼”是慕容氏对冉闵的恶谥,误也,因为“肆行劳祀”是指穷奢极欲、荒淫无耻,而冉闵即便穷兵黩武,也应与“肆行劳祀”无关)。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对慕容隽致祭赠諡予冉闵一事的评价为:“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諡,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范文澜《中国通史》) 当代权威历史著作《魏晋南北朝史纲》一书也对冉闵作出过相对中肯的评价:“至于冉闵以区区之力驰骋中原,而东晋又只作壁上观,是以亡不旋踵,只成为历史上的悲剧而已”。
四、吴又可怎么死的
因拒绝剃发而被处死,在闯军侵袭、瘟疫横行的背景下,明朝举国陷入混乱恐慌之中,百姓民不聊生。吴氏生活时代正值明末战乱,饥荒流行,致使疫病流行。1644年清军入关,清廷为巩固统治,摄政王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吴又可因拒绝剃发而被处死,妻子携子投河殉情。
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
扩展资料
成就
吴有性在书中所列瘟疫病种有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他明确指出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为。
其症状与伤寒相似而实际迥异,古书从未分别,吴氏一一加以分辨论述阐明,并论著制方。其中著名的剂方有达原饮、三消饮等,示人以疏利分消之法。
在治疗上,他提出了一整套祛邪达原理论,临床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还有他的“疠气”之说,首先肯定它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从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旧观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有性
五、吴又可的妻子是谁,历史上的真名叫什么
妻子云淑。吴又可原名吴有性(1582年-1652年),字又可,号淡斋,江苏吴县人,明代著名医家。他提出了传染病是由一种不可见的戾气所导致,由口鼻而入,与现代的病菌学说接近。他启发了清朝的温病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