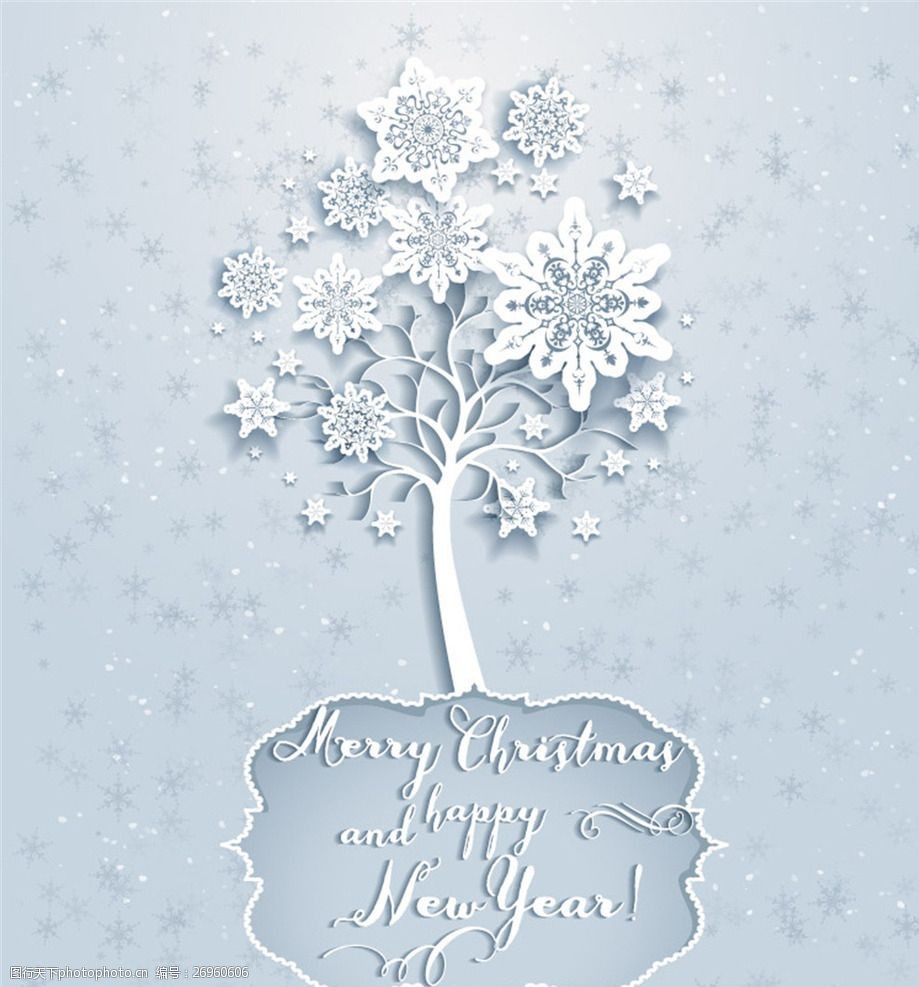一、简介一下波西米亚元素?
东欧的,德国的,吉卜赛的,墨西哥的,松松垮垮的,少数民族的,色泽暗淡的,刺绣多多的,层层叠叠的,最后使人看上去有点饮酒过量精神涣散的——波西米亚风格可是决不局限于波西米亚这个地方,它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大多了。
二、波西米亚是什么
什么是波希米亚?
答案很简单: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它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省,1918年以前还由维也纳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今天的波希米亚在捷克共和国境内,布拉格曾是波希米亚最大的城市,现在已成为了捷克的首都。过去数百年中,波希米亚常常被卷入欧洲几大政治力量的争斗之中。二战以后,作为捷克的部分,这里仍然是东西欧两大阵营的交冲之处。许多世纪以来,布拉格一直是中欧重要的文化中心,其音乐传统尤为源远流长。这,就是地理上的波希米亚。
斯美塔那、德沃夏克和杨纳切克等作曲家,以及作家哈谢克(小说《好兵帅克》的作者),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是波希米亚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有波希米亚气质。事实上,我们常说的波希米亚,严格来说并不是那个真实地存在过的国家,它只是存在于我们的脑中的一个概念,是真正的波希米亚被我们误读了的版本。而在英语世界中,这笔糊涂账一直可以算到莎士比亚的头上。
人们认为波希米亚是艺术家们的精神家园,这种想法源于另外一个对真正的波希米亚国的误解,因为人们也一度认为这里是吉普赛人的故乡,却忽略了吉普赛(gypsy)乃是埃及(Egyptian)的同源词。1843年,迈克尔·威廉·巴尔夫的著名歌剧《波希米亚女郎》在伦敦首演时,波希米亚一词就已经是吉普赛的同义语了。当时,“波希米亚人”泛指一切四处漂泊的流浪者,与艺术没有任何关系。而真正将这个词与艺术家结合在一起的,是巴黎诗人亨利·缪尔热。
1849年11月,缪尔热曾为《海盗》杂志撰写的关于巴黎拉丁区的小说《波希米亚生活情景》被改编成了舞台剧,在Varietes大剧院演出,结果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由此便在人群中掀起了对吉普赛式艺术家的崇拜之风。缪尔热的小说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术生活的范本。
在缪尔热的笔下演进和发展的波希米亚精神包含了哪些元素呢?
首先,波希米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它崇尚个体想象的力量,主张将艺术信仰世俗化。正如早期的基督教一样,波希米亚也有自己的追随者和异教徒。这里所说的追随者是那些得到了上天的点化、拥有强大想象力艺术家,而异教徒则是在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后、在大规模商品生产中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对艺术家们来说,后者是物质至上、缺乏想象的一类人,这些平庸愚昧的人永远生活在波希米亚的国度之外。缪尔热让人们牢牢地相信,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正是用于判断是否具有波希米亚气质的标准。在他的波希米亚国度中,艺术的创造不如艺术的形式感来得重要,《波希米亚生活情景》更加推崇的是吉普赛式的艺术家生活,推崇自由思想者的群居体验,而非艺术成就。
缪尔热还将“波希米亚人”的涵义拓展到了具有反传统和反体制精神的艺术家。在他进行小说创作之前的二十年里,这样的一些特征就已经出现在巴黎了。但由于在这个新时代之初的人们,尚未从混乱的物质环境中理清头绪,因此缪尔热本人可以算是第二代波希米亚人的代表,他所描绘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缪尔热说,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只存在于巴黎。的确,19世纪的英国虽然也出产了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鲁拜集》的译者)和韦达这样的怪才,罗塞蒂兄妹和威廉·莫里斯这样的唯美主义者,以及离经叛道的斯温伯恩和王尔德,但是对于整个英国来说,这几个波希米亚分子都只是特例。英国没有真正的波希米亚运动,也没有波希米亚聚居地(直至布鲁姆斯伯利出现)。安德鲁·朗在其文章《法国波希米亚三诗人》中指出,英国的大学生普遍来自上等或者中等阶级家庭,从来不知道塞纳河左岸的穷学生生活。英国学生也许会像雪莱在牛津时那样撰写宣扬无神论的小册子,也许会像拜伦在剑桥时那样讽刺社会传统,也许会一面在信念上背离正统、一面在行为上奢侈放纵,但是他们从来不可能过上那种白日混迹酒馆、夜晚宿于阁楼、以裁缝为妻、以面包屑果腹的穷苦生活。
事实上,就在《波希米亚生活》登上舞台的那一年,法国一名作家就写道,波希米亚就在巴黎的“塞纳区”,它的“北边是寒冷,西边是饥饿,南边是爱,东边是希望”。
法国小说家阿尔色纳·胡塞宣称,只要巴黎还有诗人,波希米亚精神就不会死亡。组成了波希米亚人的主体,就是各种各样的画家、音乐家、演员、诗人,以及拉丁区里的准小说家、塞纳河左岸的穷学生、自命不凡的潦倒画家和徘徊在文化圈外的纨绔子弟。
19世纪是波希米亚的黄金年代。但是随着19世纪的结束,波希米亚精神也开始日渐衰落。这群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逐渐遭受到大众的抛弃,人们不再爱听艺术青年们整日坐在咖啡馆里夸夸其谈。波希米亚气质虽然还能在学生们的身上看到,但是成年人们却不能再靠空谈艺术天赋来混饭吃。
然而,《波希米亚生活情景》并没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收场,在一战后20年代的巴黎,波希米亚风卷土重来。在二战期间再次经过一轮衰竭后,我们又能看到这股潮流在1945年之后的兴起。出于对战争时期的严酷和简朴的反抗,波希米亚精神表现在了战后女性时装对传统的挑战上。乔治·桑第一次穿上男性装束时曾让世人惊呼,但现在长裤已经成为了女性时装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风潮在男性装束上的表现则走得更过,超越了以往的尚美标准,加入了更多的女性气质。60年代的嬉皮士赤脚露足、披头散发,用鲜花和铃铛装饰衬衣,将迷你短裙和太阳镜染上迷幻色彩,一如19世纪30年代的Bousingo;那些吸食致幻剂LSD的年轻人们,则与19世纪40年代服用印度大麻的人别无二致;而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则和当年的青年法国运动如出一辙。这一切行为都似曾相识,时代背景也大抵相同。
和19世纪30年代一样,今天仍然存在着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无力填补的真空地带,今天也不可能再有一场东征运动来吸收这么多的剩余能量。但是今天依旧需要人们自我主张,需要人们寻找地方来释放能量,依旧有时刻准备着起来反抗权威的青年学生。
三、波西米亚风情是指地域风情吗?
所谓波西米亚(随便写写,莫名其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电影《红磨坊》的开头,当克里斯汀正在他的房子里用他那台旧打字机写字的时候,从他的房顶上掉下来一个人,他走上楼梯后便看到了一群疯狂的人和一个混乱的场面,当时看到这里,我身边有人不失时机地告诉我说:“那,就是波希米亚人了……”可能很多人对波希米亚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都不知道,就像很多人都不明白究竟什么才是所谓的“小布尔乔亚”一样,但不断有人告诉我们——没有波希米亚就没有现代时尚,但究竟什么又才是所谓的现代时尚呢?极端?民族?另类?复古?……可能没几个人能解释清楚。我也不知道波希米亚到底是个怎样的民族,但是我可以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披着毯子在路上挤来挤去,有时候看得出是一张精美的披肩,有时候则是那些长方的或正方的布块,既像餐桌上的桌布也像床单。
在波希米亚风格流行之前,我对波希米亚的猜测就是那些一辈子不洗一次澡,身上披着的毯子白天是衣服,晚上当被子,四海为家的那些牧人、强盗和土匪,以及贫困的艺术家和骗子,就像读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时所了解的那个嘉尔曼一样。当然,在艺术界或者某一些文化圈子里,波希米亚是一种反叛精神的象征,它被用来解释一种艺术态度,更多的人把它当成是在流浪生活中冥想人生,天性乐观的艺术家们,这足以说明在贫困面前,艺术家或者伟人与土匪强盗骗子不但不是对立的,有时候还像左脚和右脚一样相得益彰。
尽管如此,在听到波希米亚这个词的时候,我依然热血沸腾。这种热血沸腾就像是得了熊掌的人听到别人还许诺了鱼,双喜临门。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自由,波希米亚吹过来的风是这样说的。那些在底层社会挣扎的人为什么贫困,因为他们边缘,只有当衣不裹体和自由形成了对立的时候,人们才不得不在鱼和熊掌之间做出选择。跟随主流当然就是安全的了,如今,当波希米亚在巴黎、米兰、纽约这些高级时装发布会里出现的时候,它就从边缘就变成了主流,也就是说那些边缘的反叛被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认同了。没有人去管这种风格到底代表了什么,也没有人去管这种看似浪漫的生活态度原本的起因,是怎样一种饥寒交迫和身不由己。
当权威设计师把波希米亚风格变成春夏时装发布会里的一种风格的时候,时尚评论界开始号召人们穿得像个波希米亚人、时尚媒体也开始宣扬:让我们波希米亚起来。看来这倒是个不错的潮流,早上起床晚了,卷着床单去挤公共汽车也将会成为一种时髦的装束,没有人会侧目。波希米亚进入了主流,就好像终于把野兽驯成了家禽。本来是在荒野中无助的吟唱,最后渐渐变成了红男绿女们酒足饭饱后的消遣,这种变化看似一种驯化,其实是完全和原著不同的,照本宣科的另外一种风格的诞生,如果要给它一个定义,我们不妨说它是“伪波希米亚”,因为真正的波希米亚人还是那么的生活着,无论有多少狂热的摹仿着他们的人在高喊——我们是波希米亚一族。同样,也因为这种虚荣的态度,很快地,对波希米亚这个民族或者这种精神的向往,以及他们曾经给艺术或者文化带来的清新空气,就一步步变得恶俗起来,就像“意识流”,“后现代”,“抽象派”等等有独特思想的东西最终沦为标榜个人品味的标签一样。当摆地毯的小贩们向你推荐一块破抹布并称其为波希米亚披肩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怀疑?那不就是波希米亚么,没有教条、没有束缚、没有传统,这一切让人没有理由不相信——恶俗其实也正是波希米亚风格的一部份。
如果有一天,时尚制造者们发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经历也是浪漫的,说不定又会制造另一种MHC风格呢?对不起,这个MHC就是“卖火柴”的拼音缩写,有点跑题,还是让我们继续说我们的波希米亚风,波希米亚的伟大在于,把每一个平民生活全部搬上精英舞台,把底层文化归顺到主流的队伍,著名的时尚品牌“香奈儿”用假珍珠项链来延承它一贯的优雅,波希米亚就这样和贵族达成了不可告人的协调。最终谁会据守波希米亚这片理想的自由天空呢?是贵族还是平民?不管怎么说,波希米亚服饰的流行,终于实现了阶级的平等。只是当每一位为了赶上潮流的人身上披上上波希米亚的披肩的时候,波希米亚的创造被模仿和复制,穿街过巷,波希米亚就只不过是一个类似“绿色食品”一样的标记了,人们可能是为了你有这个标记而买你,但并不代表相信了你。
我记得当有人问一位著名登山者为什么要去一个接一个的攀登险峰的时候,他回答了这样一句话“Because the mountain is there……”——因为,山在那里。我一直钦佩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人,因为他们决不妥协也决不伪善,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如果有天堂,而我们无法到达,那绝对不是因为山高路远。我们非常善于挥霍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我们把它变得日常并视为己任,不管什么一旦变得日常,得到的最后一句就是:天堂不过如此,永远也到不了巴洛克,而波希米亚却不可能一直流行下去。当然,还会有“波波一族”或是“丁克一族”承继着这些风雅人士的理想,但是,当披着有餐桌布嫌疑的毯子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办公室、电影院、KTV、咖啡馆等地方浮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走投无路起来,因为连最后一个想去流浪的地方都没有了,不知道当撒哈拉变成像桂林山水般的旅游热点的时候,曾经万水千山走过的三毛,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感慨。今天在这里胡说八道半天,估计很多人都不明白我究竟想说什么,我只有一句一直想说但始终言不由衷的话——流浪和浪漫,真的不是一回事。
地名
波西米亚风与BOBO族
波西米亚在哪儿?这问题可真是难以回答。它好像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什么地方,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你不必因此而愤怒谴责我的草率和不负责任——相信我,在这个季节被时尚人士整天挂在嘴边的波西米亚风格跟地理上的波西米亚并没有什么大关系。
波西米亚。波西米亚。波西米亚。
这个词语每天在我耳边此起彼伏。各大品牌的PR告诉我他们这季节的设计是波西米亚式的融合风;我们的时装编辑铆足了劲头要制作一组波西米亚式的时装片;有一些女人和女孩子,她们兴致勃勃地打扮起来,出现在一些时髦的派对和时装秀场,“你是不是认为我今天看上去很波西米亚?”在我开口之前,她们先对自己做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说法。
究竟什么是波西米亚风格?
东欧的,德国的,吉卜赛的,墨西哥的,松松垮垮的,少数民族的,色泽暗淡的,刺绣多多的,层层叠叠的,最后使人看上去有点饮酒过量精神涣散的——波西米亚风格可是决不局限于波西米亚这个地方,它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大多了。
TOM FORD为圣罗兰设计的土耳其式豹纹长衫据说是今季波西米亚风格的代表。虽然它看上去实在是太奢华了,远远超出了一个真正波西米亚人对于华丽生活的想象,可是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在一开始就讲过,波西米亚风格跟波西米亚没什么大关系。
像波西米亚风格这样的专有名词近来出现很多。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谁发明了谁。或者说谁被谁所诠释。除了国籍民族肤色性别年龄的区分之外,有些人群需要一些独特的称谓来划分。基本上,那是一些所谓特立独行的动物。
比如说BOBO。这是去年的热门词语。文化学者把他定义为是嬉皮与雅皮的杂交品种。像嬉皮那样的叛逆精神,也可以有适当的颓废,大麻是允许的,毒品是反对的,同时还有体面的工作,优越的收入和良好品位。
据说一个真正BOBO的标准行头是这样的:穿着几千美金的GUCCI皮衣和几十块钱的LEVIS牛仔裤,他的头发乱乱的,仿佛有三个月没有打理过,可是他的身上散发着适当的香水味道,他习惯穿廉价而舒适的运动鞋,可是他对于他的内裤无比讲究。
哦。听上去还不坏。甚至是令人心动。正邪一体。双面共聚。这样的BOBO,无论男女,必定横扫千军所向披靡。
如果没有由于网络而诞生的新贵们,BOBO这个词语还会不会出现也是疑问。没有比这个行业的人士更BOBO了,那些网络新贵哪一个不是些疯狂艺术家和奸诈商人的混合体。看看比尔·盖茨乘着私人飞机住着5星级以上的酒店,并且穿着让时装编辑作呕的,很像是来自廉价商店的T恤和仔裤——BOBO就是这么肆无忌惮,够自由,够歹毒。
那种丝毫不顾忌别人的令人艳羡的歹毒。
波西米亚风跟BOBO似乎是薪火相传,至少,它们是近亲关系。它们的精神都是强调人的艺术气质、叛逆和自由,这是大众还是设计师的爱憎取向?又有多少人具有或者真正渴望艺术、叛逆和自由?结果是我在许多场合看见无数人打扮得像是街头为人画肖像的潦倒画家,或者就像个鬼鬼祟祟的特异功能人士。
也许在这时刻人们难免堕落。全球经济不好也已经有很长时间,911的阴影刚淡下去,中东又开始刀光剑影,——许多我们原本以为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其实沉甸甸地压在心里,然后一有机会就蔓延起来。
岂止是蔓延。这简直就是腐蚀。
当然也有令人愉悦的腐蚀。
就像我们享受BOBO风或者波西米亚风或者吉卜赛风,无论什么流行,我们一律愉快接纳。时尚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以万变应不变。
谁可以预测下一次的流行吗?
说不定是布尔乔亚的爆炸颠覆。那些我们脑海中沉闷乏味教条的中产阶层形象也许快要过时,你可能再也不能这样去看待他们。如果布尔乔亚们抓起狂来会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疯狂的方式。而时尚动物们永远是各种集体疯狂的参与者。
又怎样?
至少现在你可以说:
“我很波西米亚,而且,我很快乐。”
作者:Rainbow
-- 发布时间:2003-3-13 12:11:00
-- 波西米亚
Bohemian,一般译为波西米亚,原意指豪放的吉卜赛人和颓废派的文化人。然而在今年的时装界甚至整个时尚界中,波西米亚风格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浪漫化,民俗化,自由化。浓烈的色彩、繁复的设计,会带给人强劲的视觉冲击和神秘气氛—实际也是对这两年简约风格的最大冲击。
三毛说,台湾只有三个女人适合波西米亚式的打扮,她们是潘越云、齐豫和——她自己。想想也是,她们三人虽然妍媸有高下、术业有专攻,但无论是言行还是气质总有一些相似之处,都属于那种特立独行、才华横溢而又总是不想受现实规范约束的类型,在装扮上喜好一致也就不奇怪了。她们总是穿着松松垮垮的棉质长裙,戴着层层叠叠的大项链,抑或还有样式古怪的平底软靴和大胆花俏的额饰,环佩相扣、叮叮当当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她们的这种装束可以一言以弊之——披披挂挂,当然,换个好听的词就是今天的主题——波西米亚风格。
什么是波西米亚?是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个放荡不羁、以歌舞为生的民族,还是指那群视世俗准则如粪土的艺术家?发展到今天,却成了一种生活观,在波西米亚的旗帜下,一向为新生代不耻的老布尔乔亚的理想——追逐财富,和波希米亚崇尚自由的精神不可思议地结合起来,向人们展示着一幅用庸俗作背景的个性场景,也许这正是现代精神的一个侧面:除了金钱,没有什么能让人获取更大的自由。有人用一句通俗的时尚语言精辟地概括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小资情调——原来如此!
再复杂的情绪,在这个时尚的时代都能用感性的服饰演绎出来,波西米亚落实在女人身上,便成了一种奢华的另类、个性的高贵。
波西米亚风格的装扮,在总体感觉上靠近毕加索的晦涩的抽象画和斑驳陈旧的中世纪宗教油画,还有迷综错乱的天然大理石花纹,杂芜、凌乱而又惊心动魄。暗灰、深蓝、黑色、大红、桔红、玫瑰红,还有网络上风行一气的“玫瑰灰”便是这种风格的基色。没有底气的人一穿上便被无情地淹没在层层叠叠的色彩和错觉中。
一说波西米亚,逃不了一条打满粗褶细褶的长裙,它可以是纯棉的、粗麻的、砂洗重磅真丝的,可以是镂空设计的、缀满波西米亚式绣花的、加上婀娜的荷叶边的、垂垂吊吊满是流苏的,可以是布满无规则图案的、用其他风格面料拼镶的……总之它是繁复的、奢华的,无时不刻在昭示着自己独特的,它让穿上它的女人刹时间变成超凡脱俗并蔑视一切。
如果还要披上外套,那最好是一件收腰收得恰到好处的长大衣,昂贵的羊绒当然是第一选择,退而求其次便是精纺亚麻,加一条粗犷而帅气的腰带,将硬朗与柔美完美地结合起来。
还有饰品,不能不提的波西米亚饰物,要做个地道的波西米亚女郎,你最好不要放过身体上任何能披挂首饰的部位,手腕上、脚踝上、颈前、腰间,还有耳朵、指尖,别人戴一串,你戴三串,别人挂细的,你就挂粗的,这两年疯狂流行的藏饰被波西米亚女郎们引为至宝,那些发黑的银器、天然的或染色的石头,哪管它重不重、贵不贵,统统往身上手上套了再说。走动间,一定要浑身上下泠泠作响;点烟时、端起大扎啤酒时,一定要让连着戒指与手镯的链子斜斜垂下,勾着男人的眼光晃啊晃,一直晃到他心尖尖里让他脱身不得。
啊哈,美丽的波西米亚女郎,你最好有着模特儿一般的身高,如果你个子不够高,那一定要身材苗条;如果你偏巧有那么一点胖,那至少要有气质;如果不幸你的气质也不够加分,那无论如何谈吐要字字珠玑;如果……唉唉,你还是死了这条波西米亚的心算了。
参考资料:;ID=1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