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县的著名人物
太和县的著名人物有高警寒、吕范、徐子佩、朱荫桐、徐广缙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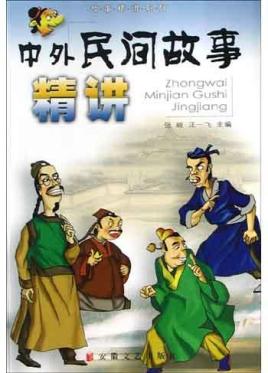
1、高警寒
高警寒(1902.12—1996.6)男,旧县镇高小庄人,幼年在旧县小学读书,1919年到阜阳省立第三师范读初师,1923年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
2、徐子佩
徐子佩,税镇镇渔池村人。幼年读私塾,13岁进入新集渡口小学,15岁就读于河南省开封中学,后转学到南京。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
为了响应党中央去苏区工作的号召,徐子佩前去上海,由于党中央正在开展反立三路线斗争,未能与组织取得联系,又返回北平,被市委任命为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
3、吕范
吕范(?-228年),字子衡。汝南郡细阳县(今安徽太和)人。汉末至三国时期吴国重臣。
吕范年轻为汝南县吏,后避难寿春,结识孙策。此后随孙策、孙权征伐四方,对稳固孙氏在江东的统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孙权将其比之于东汉开国元勋吴汉。吴国建立后,吕范累官至前将军、假节、扬州牧,封南昌侯。
4、朱荫桐
朱荫桐,男,字葆华,曾用名朱保,太和县旧县集人。曾任安理工大学动力系任教授及教研室主任。
随着国家对高等学院院系的调整,先后在西安动力学院动力系、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陕西工业大学(现更名为西安理工大学)动力系任教授及教研室主任等职务。1965年,在骑自行车上课的路上摔伤致脑震荡,后因脑震荡后遗症退休。
5、徐广缙
徐广缙(1797~1869),字仲升,一字靖侯。安徽太和大新镇徐寨人,清嘉庆年间进士, 选庶吉士。历任山东,陕西道御史,广西乡试正考官,榆林知府,江西总粮道,福建按察使,顺天府尹,四川布政使,江宁布政使,云南巡抚,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和两湖总督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太和县
安徽省太阜阳市太和县的历史故事
太和,古为豫州之域,春秋时期属宋国,名鹿上,又名邢丘、廪丘,宋国曾与齐国、楚国在此会盟,称为鹿上之盟。
战国时期属魏国,苏秦说魏襄王“南有新郪”,即指太和。后归楚国。
秦统一后,置新阳县,属颍川郡。
汉置细阳、乐昌、新妻宋,并属汝南郡。高祖二年(前205年),益封汝阴侯夏侯婴细阳千户。高后二年(前182年),封赵王张敖子寿为乐昌侯。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封外戚王武为乐昌侯。
东汉光武建武十一年(35年),封陈彭子陈遵为细阳侯。建武十七年(41年),以军功封郭亮为新妻侯。章帝建初四年(79年),徒封殷后宋公于新妻。
三国时属魏,废宋公国为宋县,景初二年(238年),隶属谯郡。
晋废细阳。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将宋县改属汝阴郡。宋、齐属西汝阴郡。北魏太和间(477年―499年),废宋县。梁置陈留县。
隋改陈留为颍阳县。
唐贞观元年(627年)废颍阳,并入汝阴(今阜阳),境内置百尺镇(今原墙)。
宋开宝六年(973年)于汝阴县百尺镇置万寿县,属颍州。宣和元年(1119年),更名泰和县,移县治于沙河北岸(今旧县镇)。绍兴末陷于金。金亡,复归宋。
元至元二年(1265年),省泰和入颍州。大德八年(1304年),复置县,改“泰”为“太”,县治迁于今地,属颍州,后属汝宁府。
明属南京凤阳府颍州。
太和洪山的历史故事
太和洪山镇祝楼村一带居住着近万祝姓人家,其近世先祖系宋户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祝维岳。其四个儿子全部为进士出身,第四子祝谘后裔祝玢、祝岳于明洪武三年迁徙太和洪山,至今已有540多年历史。
始迁祖源山东成武
1993年太和洪山祝氏与山东成武祝氏联合续修的《祝氏族谱》载:《成武县志》载,宋乡贤祝维岳,显达官户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正一品)。四个儿子也相继中了进士,长子祝谏,屯田员外郎;次子祝诰,官蔡州县令;三子祝许,知并州军事观察推官;四子祝谘,官太常寺少卿,世称“父子五进士”。此父子事迹成武县西北十五里白店有墓碑可考。
目前在山东省成武县伯乐集镇白店村西黄楼村南现存宋熙宁七年(1074)所立惟岳公墓神道碑一座。碑堂内存有清雍正四年(1726)所立维岳公墓碑一座,另有民国十四年(1925)所立谏公、诰公、许公、谘公墓碑。维岳公墓神道碑记载:祝维岳,字同甫,成武县伯乐集镇白店村人,宋景德二年中明法科进士,出任陵州司理参军,后任秦州观察推官,大理寺丞知河中府龙门县,为一代名吏。去世后被皇帝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祝维岳后裔分别居住于山东省成武县、定陶县、曹县、单县、东明县、滕县、鱼台县、微山县,河南省商丘、民权县、兰考县、虞城县、太康县、永城县,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沛县、铜山县、阜宁县,安徽省太和县、界首、宿县、淮北、砀山等地。
成武县以祝维岳为始祖,以下祝谏为长门、祝诰为二门、祝许为三门、祝谘为四门。一、二、三门在本地都有延续,唯四门祝谘之后一直没有联系。一说“祝谘丘由单州城武(今山东成武)徙居滑州韦城(今河南长垣),”一说徙居河南固始等地,一说徙居安徽太和。这里的祝谘丘就是祝谘。从现有资料看祝谘的后代应在南宋时期以后历代迁徙出去的。
自宋帝十八世徽钦时金人南侵,南北混战,国无宁土,祝氏有随黄帝南迁者,有避兵乱逃亡四方者,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江苏丰沛、河南固始、民权,安徽太和、山东省曹县滕州邑县巨多。祝维岳后裔自山东成武乘马车到颍州太邑北七十里祝老家园,聚族而居。生五子,分别为金、银、铜、铁、锡。祝金居界首大桥集祝楼,祝铜居洪山祝楼,祝银、祝铁、祝锡居祝瓦房祝老庄。
居住祝楼的祝先森介绍,1992年9月10日山东省成武县族人祝以佛、祝兆森二人来太和县联络祝氏,经查考世别,翻阅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太和《祝氏族谱·序》(2010年清光绪《祝氏族谱》失窃),方知太和祝氏这一支系实成武近世始祖祝维岳第四子祝谘之后裔。
山东成武县东十八里苟村集近世一世始祖祝维岳;二世祖祝谏、祝诰、祝许、祝谘,成武县西北乐村白家店故里,庄西里许先祖坟茔在焉,尚有墓碑可考。昔经金元之乱,谱毁于兵燹自三世祖以下失传者八世,至元代只有祝彦昭迁居大双固集世系始可纪。
十一世祖祝彦昭,敕赠奉直大夫;十二世祖祝守贞,敕赠奉直大夫;十三世祖祝语,明工部都水清吏司,员外郎,诰封奉直大夫,南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苟村集西里许仍有坟莹墓碑可考。碑文字有:“天顺二年岁次戍寅秋七月,奉旦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员外郎祝语”。
十四世祖祝执和祝同,祝执也名祝寿,明深州通判。祝同,明进士迁居定陶城东祝楼。十五世祖祝芹,衢州罕知事;十六世祖祝永孝,庠生入孝子祠;十七世祖祝继先和祝景先,祝继先监生,祝景先儒生诰封中议大夫;十八世祖祝康(官中书舍人)、祝瑞、祝肃;十九世祖祝尚礼、祝尚智(无嗣)、祝尚信。
二十世祖祝方明和祝方元。祝方明生五子,长子祝尔奉,次子祝尔禄,三子祝巽南,四子祝尔公,五子祝尔侯。祝方元六房夫人,大夫人生子祝尔福;二夫人生子三子:祝炽、祝昌、祝寿,三夫人无子嗣(养祝而寿次子祝朋为嗣孙),四夫人生二子:祝尔承,养子祝尔艾(系外甥),五夫人生一子祝尔猷;六夫人生一子祝尔兴。山东成武县祝氏至二十一世至今,世系派别清晰,不再赘述。
太和祝氏宗谱曾于清代修谱,因黄水泛滥,老谱失没,兵荒马乱,祝金、祝银、祝铁、祝锡四门老谱无存,仅有始迁二世祖祝铜一门老谱尚存。1992年由山东祝氏族人联络聚会,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十余县城的族人汇集成武县,于1992年8月至1993年3月完成《祝氏族谱》十一卷修谱任务。
我们由祝氏家谱史料可知,太和始迁祖祝玢、祝岳二兄弟系山东成武县近世一世祖祝维岳第四子祝谘之后裔。祝谘为近世二世始祖,其后裔祝玢、祝岳因家谱失传八世,如按失传八世辈份推算,则约为近世十世祖,也即太和县洪山镇祝楼祝氏的始迁祖。
祝楼始迁祖玢、岳兄弟
明洪武三年(1470年),祝玢,祝岳兄弟二人自山东成武迁至颍州太邑(今太和)北七十里。据祝氏老家谱记载兄弟二人共五子,分别为金、银、铜、铁、锡。后来长子祝金迁界首定居;二子祝银居太和洪山镇油坊庄;三子祝铜居洪山镇祝楼村;四子祝铁,五子祝锡仅知也居洪山镇油坊庄,但老家谱丢失后,后裔世系无法理清。
如今祝玢、祝岳两位始迁祖后人居住分布在太和的祝老庄、祝瓦坊庄、祝油坊、前祝油坊庄、后祝油坊庄、祝坊庄、文铜寺、小祝庄、祝碱场、三里桥、祝计庄、编筐庄、祝楼、祝西楼村、祝庄、北祝庄、原墙镇祝庄,以及界首大桥集祝楼、马提桥口等等。界首有部分族亲寄居河南鹿邑等地。太和祝氏辈分目前可知的为:“尧、九、应、从、立、祖、 先、本、尚、陪、儒、世、心”。洪山祝楼祝氏堂号为“勤贻堂”。
今天的太和县洪山镇油坊行政村祝玢(芬)这一支系目前可考者:十九世祝文明,二十世祝承琏,二十一世,祝凤阁、祝凤台。二十二世祝治德、祝治巳;二十三世祝洁、祝显、祝凯;二十四世祝尧奇、祝尧松、祝尧智、祝尧相、祝尧凤、祝尧太;二十五世祝九朋、祝九增、祝九善、祝九惠、祝司臣;二十六世祝应才、祝应双、祝应运、祝应有、祝应志、祝应绪、祝从冉、祝从富、祝从宪等等。二十七世至今已至三十三世,世系派别谱载基本清晰。但因为是20纪90年代修谱仓促,加之一些过去划定为地主成分的家族人士担心害怕,而没能入谱。
祝楼村75岁的祝立然老人告诉记者,他高祖爷祝应郎,曾祖祝贤武,祖父祝庆址,父亲祝从起。他说,祝氏从明代迁徙至太和后建有有祝楼,非常高大宏伟。
走近祝楼村
8月23日,市直干部祝祖良陪同我一起坐车前往太和洪山镇祝楼村。洪山镇南与倪邱镇接壤,北邻河南郸城,离太和城区七十里。
祝楼村位于黑茨河北岸,太和洪山镇管辖,因古时候有多处楼房院落而得名,全村有300多户人家,均同族同姓。
祝立然老人回忆,楼院始建于明代中期,距今约有500多年的历史。盖祝楼院落用的大青砖都是用秫秸(高梁杆)烧的,砖烧好后几百个人排成队,从一公里外的窑后陈庄南地的窑场传过来的。楼院主人家的祖坟在二里外的倪邱镇文铜寺一带,可知见当时楼院主人的良田之多和富有。
祝楼建筑原先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处院落,东南院、西北院及南牌坊早年毁坏。西南院落于1948年因一场大火而倒塌。东北院落文革时期虽然遭到破坏,部分建筑构件被拆掉,但整体完好。1957年因建洪山大礼堂及祝楼村中学用砖,把三间两层、二进院落,两边各有厢房的祝楼拆除,前客厅因当时有人居住未被拆掉。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因两家房主人翻盖新房拆除了前客厅,部分砖雕、木雕等建筑构件用在了新建筑上被留存了下来,一块堂匾用在了门板上。现残存墙体一段,为大青砖垒砌,墙厚约六七十公分,缝隙为糯米饭渗草木灰浇灌,中间为松散夹层,应为保温防潮之用。
记者看到,村内青灰色碎砖烂瓦随处可见,明清时代特征明显。几个散落在草丛里的青石鼓不同于常见的扁石鼓,而是石础,即固定在大木柱子下面的石头,也称柱石。一堵青砖残墙掩没在荒草丛中,祝楼村民院中随处散落着各种带有花纹图案的残砖碎瓦块。村内还有早已干涸的两口老古井,遗址还能看到。村里上年纪的老人都说,祝姓是明代从山东迁到这里,原村名为李瓦坊,后盖起了院楼才改名为祝楼。
祝楼村周围的地名也能佐证其历史悠久和楼院的存在,南园顶、南牌坊、西庄户、东西南北寨墙、寨海孜、寨门口、东敌楼等,全村老少人人皆知。祝楼因坐落在黑茨河北岸,古时候交通便利,水土肥沃,人们生活富裕。当时一个村庄有多处楼房院落,在皖北地区也很罕见。据说在明代有万亩良田者,可得到皇帝题字嘉奖,祝楼村现存的“勤贻堂”牌匾出自何人之手,因字迹被毁无从知晓。
市直干部祝祖良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在祝楼生活成长,对于祝楼的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感情。尤其是对雕梁画栋、巍峨宏伟的祝楼更是产生了深深的怀念。他说,祝楼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目前散落存在祝楼村周围的各种石雕、砖雕、木雕,以及祝楼古建筑遗址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亟需历史考古界进行挖掘和整理。
祝氏的得姓起源
综合《竹书纪年》、《新唐书》、《姓谱》、《元和姓纂》、《中国姓氏起源》、《中国姓氏辞典》等载,祝氏起源有三:
一是以国为氏。出自有熊氏,为黄帝后裔。西周初,周武王分封先代遗民,把黄帝的后人封于祝地,其地望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建立祝国。春秋时祝国亡于齐国,原祝国人则以国名为姓,成为祝姓。
二是以职官为氏。古时设有专门负责祭祀时致祝祷文辞和传达神意的官职,称作巫史,也叫祝史,故后有祝史氏,《姓谱》载“卫有祝史挥”。祝史官的后裔有的以职官第一字命姓,为祝姓。《元和姓纂》载:“古有巫、史、祝之官,其子孙因以为氏。”又有祝宗、祝丘、祝和氏,皆上古火帝祝融之后裔。祝基,出自子姓,是宋国君戴公之子公子其之后,祝其官大司寇,子孙用祖名命姓为祝其姓。见《路史》、《风俗通》。
三是出自他族改姓。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北魏叱卢(吐缶)氏之后有祝姓;清朝满洲八旗姓爱新觉罗氏、喜塔喇氏等之后均有改姓祝者;傈僳族以竹为图腾的麻打息氏族汉姓为祝;今满、瑶、彝、土家、蒙古等民族均有此姓。
太和洪山镇祝楼祝氏尊山东成武县北宋祝维岳为近世一世始祖,宋代以前先祖无考,无法攀附。山东成武县二世祖祝谘后裔祝玢、祝岳二兄弟自明洪武三年迁徙至太和洪山建祝楼,为今天洪山祝楼祝氏的始迁祖。
太和县关集镇的小满会作文400字
说起农村的“集”或者“会”,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从古代就兴起的这种民间买卖和商品交易方式一直流传至今。河南的大大小小城镇,延至不太起眼的村落,都时兴着的各式样的集会。
自我童年记事起,家乡最有名的集会就是“小满会”,有的村子叫着叫着就叫成了“小麦会”。乡亲们称作小满会,这里是有讲究的。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上记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在中原地区,这时麦类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顺口说:“小满物满盈,小麦快长成。”小满会或许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村里的老人说,小满会是小麦收割前的一次大集会,更像是一种收割作物前大动员活动。
一直以来,小满会固定在距离我家三四里路的巨岗村举办。巨岗村地处黄河北岸,毗邻106国道,交通便利,它不但是周边乡镇通往开封、郑州的必经之路,也是周围村落之间往来的要道。这村做生意的也多,能人多,用今天的话说,村里有经济头脑的人多,慢慢的,村子就演变成一个类似城市“商业中心”的地方,功能就像现在的二七商圈之于郑州一样,它辐射周围的村落。我问过村里的老人,小满会啥时候开始在巨岗举办的,老人都说,“这会啊,年太多了,早一辈都有啦,记不清楚是那一年了。”
一年一次的小满会,依据每年季节日期有所调整,一般在阴历4月14日举行,15日结束,别看时间短,这两三天可谓是人山人海,浩浩荡荡,整个集市从村西头到东头蜿蜒三四里路,商户依据路两边的杨树、柳树或者预制板等搭建商棚,规模大小不一,那场景用“热闹”、“壮观”等词来形容都不够准确。有个小细节透露一下,有些生意个体户为了抢占先机,提前两周就开始占位了,竞争激烈,似乎是这大集会来临前的预演。
讲了这么多,恁也别嫌烦,下面就带您赶趟小满会。
记忆里,小满会当天清晨饭后,村里人就开始“蠢蠢欲动”,家门口套架子车的,院子里叮叮咣咣收拾东西的,妇女们嚷叫交代着男人买这买那的,孩子们兴奋的追打着,姑娘们在谈论着买啥款式的裙子,老人们也换好了干净的衣服静坐在门口等着出发了。
不大会儿,村子里就真正的热闹起来,人们出发了,坐马车的,骑自行车的,还有结伴步行的,都一股脑的汇聚在从村里通往小满会的那条路,像流水一般涌向小满会。若是赶巧碰上对面的村子出发的乡亲们,两股人群很有气势的朝着106国道汇合,那场面像是古代交战的双方开打一样,各有各的阵势。等到两队人马汇合在106国道,人群掺杂在一起,两个村的乡亲们开始互相打招呼开玩笑,一时间,这支大队伍熙熙攘攘,人群里散发着异常的兴奋和无法形容的热情,载着这样的巨大希望一路向北。
十几分钟后,大队伍陆陆续续的到达巨岗村口,村口处聚满了人群和马车、自行车以及少量的拖拉机。我们这支队伍开始也陆续的解散了,栓马车的,锁自行车的,男人自成一队,妇女、孩子、姑娘们结伴而去,老人们则被送到会场的外围去看戏。
说到这里,就算进入小满会场了。
啥?流着油的金黄火烧?
刚进村口,孩子们就赖着不走了。路两边有几家卖火烧的摊位,摊位前围满了人,一股股的葱花肉香味溢散开来,那时候,光是闻着这味道,我们这帮孩子就开始流口水了。等到靠近烧饼炉,瞧见铁炉板上那金黄的滋润着油花、发出滋滋的声音的火烧,我们就彻底迈不开脚了。即使站在一旁看着,也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来一个吧,孩儿?你要不要来一个?好吃不贵啊!随着胖胖的老板娘那一声声吆喝,孩子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一个个都不停地央求着家长买火烧吃。为此,有的孩子还大哭大闹起来。这会还没有开始逛,就率先在这热闹起来了。
留光火烧,在我们那特受欢迎,据说,正宗留光火烧都已经卖到首都北京。在附近的乡镇和村落的集会上,很多卖家都是模仿着留光火烧去做的,且不说正宗不正宗,反正是味道好极了。很多时候,我们小孩子赶会就是为了能吃上一个火烧,只要手中拿着一个火烧,再拥挤的人群,再热的天气我们都能忍受。
吃一回就上瘾的硬菜,猪头肉
说到吃的,人人都难例外撇开。这不,男人们挤在了猪头肉的摊位前。当时,巨岗猪头肉在我们那一带可谓是“美名远扬”,是难得的一道“得劲”的下酒菜。老板和几个徒弟站在小店的摊位前,面对囔叫着的人群,手脚都忙不过来。这些乡亲们也顾不上先来后到,谁都想抢先买到刚出炉鲜嫩的猪头肉。用今天的话说,就跟大家节日里参与疯狂的网购一样,人人卯足了劲,看谁手快。
猪头货(猪头肉的俗称)也是家里请客吃饭的一道硬菜。逢上请人吃饭,特别是重要的亲戚或者客人,主人都会特意上一盘猪头货,客人喜欢吃这一点咱先不说,重要的是主人显得有面子。一盘猪头肉放在桌子中间,就这么一放,主人心里敞亮敞亮的,倍有面儿。其实,那时候很少有人专门买着吃,也就是逢上会或过节、请人吃饭才会享受一顿。当时,凡是能沾光吃上几口猪头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现在巨岗猪头货已经走向市场,取名巨岗卤肉,在开封、新乡等城市比较受欢迎。
一应俱全的农具天地
沿着这条会场主路往里走,就泾渭分明了。路北的人群多是男人们,路南则是妇女和孩子。这是我记忆中的小满会最有特色、最难忘记的画面。
会场主路北边,是一家家的农具商户,这些农具商户是依靠着路边的杨树、柳树、预制板等搭建农具摊位。沿着这些摊位从西往东一眼望去,只见一排排溜光的大木杈,几乎跟树一样高、一样蓬勃的大埽把,锋利的月牙形的镰刀,还有做工精细的木耙、木楸、篮筐、簸箕、笆斗、麻绳、卷席、草帽等,这些都是收割麦子必不可少的工具。顺着在看下去,还有铁楸、锄头、爪钩等铁质农具。男人们聚集在这里“摩拳擦掌,叮叮咣咣,跃跃欲试”,挑选合适的农具。就这么一圈转下来,有的人高兴的扛着几个大木杈,有的买了几个卷席,卷席是为了屯麦子用的;还有的人几乎件件都买一个,两手早都拿不下了,说法是又是新的收割季,换套全新的吧,这样的话,一是新农具好用,二来干活来劲。
在农具商户的后面,是一片荒地,荒地里遍布杂草,也有稀疏的杨树。这里是牲畜的交易场所,比如骡子、牛、驴、猪、羊等等。牲畜交易场所的人相对少一些,多是中年男人或者一些上岁数的老人,他们经常与牲畜打交道。这里的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困难一些,比如,商户一个劲的夸自己的驴多好,多卖力,而围在一旁有意向买的人则不急,他们抽着烟,一根接一根,围着几头驴来回的观看,时不时的摸摸,或者拍打几下驴,像是满意又像是不太满意,一副捉摸不定的样子。这时,商户干着急也没有办法。
牲畜交易场所最吸引人的是专门给牛治病的地方。人们围成一圈,一头牛拴在木桩子上,几个人按住牛头,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男人将一个特制的磁铁塞进牛嘴里,继而磁铁进入牛肚。约十分钟后,中年男人将手里的绑住磁铁的线握紧,同时,一面慢慢的往外拉回磁铁。这时,周围的人都有些紧张。还好,中年男人将磁铁轻巧的取了出来,只见磁铁上吸附着碎铁皮、铁屑和其他一些金属颗粒。这时,人们开始说说笑笑,气氛欢快起来。这个过程,真是让我们长了见识。
绚丽的花布世界
路南多是卖布料、衣服、水果以及其他小吃的摊位,可以说是女人们的天地。一列列整齐的色彩鲜艳的花布依次排开,顺着一个方向望去,仿佛身处一个五彩斑斓的绘画世界,看的人眼花缭乱,这“花花布构成的绚丽地带”与路北边灰色的农具天地形成强烈的对比,此时,你若是从空中俯瞰,会场主路一半是灰色,一半是彩色,像画家笔下的新旧两个世界。
布料是女人们必买的,用来给男人、孩子做衣服。当时,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手工做的,很少买成品衣服。那时,我跟在母亲身后,母亲和其他婶婶、大娘们在布料等摊位前挑来挑去,不厌其烦,当你觉得她们已经谈妥准备购买,商户早已拿着剪刀和尺子丈量布料的时候,她们却撂下手里的布料继续往前走,你只能眼巴巴的跟着往前走,她们总说“前面还有更好的。”
妇女们领着孩子,一边看花布,一边还要留意孩子不能走散;只见她们跟商户讨价还价的,打孩子的,还有互相吵架的,总之,乱哄哄的,可比路北边热闹多了。
路南边人群很拥挤,结伴同行的人稍不留意就走散了。这里插个小故事,有一次,姐姐不小心在一个路拐弯的地方走散了,母亲吓坏了,她在人群里仔细又焦急的寻找着,碰上村里人就嘱咐人家若是见到我姐就先领着她,这样,村里人你传我,我带话给你,消息像一条弯曲的线散播,姐姐就像是在这条线的某一处待着,只是暂时与母亲隔断了,最后,姐姐被村里人找到了。母亲看到她时,她已经哭成泪人,哭的全身都湿透了。邻居对母亲说,丢不了,会上都是咱村的人。
老年人的专属大戏台
热闹和拥挤的会场,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是个难题。所以,他们更乐意前往大戏台安静的看出戏。他们赶会跟小孩子赶会一样,目的很明确,小孩为了吃,老人就是看戏。大戏台就在会场主路南边一个大空地搭建起来的,戏台周围还有一些小孩子喜欢的游戏,玩具摊位,以及一些吃的,例如胡辣汤,凉皮啊等。
那时,我很少去大戏台,因为一句都听不懂。后来明白,大戏台是为了关照老年人而专门搭建的,一来不至于忽视他们这个群体,是村里沿袭下来的一种尊重、孝敬老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大戏台是地方戏剧文化的一种传播载体,也是地方文化的缩影和体现。
走到这里,基本上就算走完热闹的地方。当然,这不是家乡的小满会的全部,有些感受和细节是无法见诸于文字的,至于其中的意味,只有我们本地的乡亲们明白,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近些年,小满会还是一年举办一次,规模也很大。只是人相对少了些,人们的热情也低了些;商品类别变化很大,原来的最有特色的农具几乎看不到了,替代的是现代农业大型机械工具。
其实,早些年人们赶小满会(小孩子除外),乡亲们更多是一种心理期盼和希望,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麦收而购买农具,农具在手,收获就有,希望就有。一个热闹的小满会,昭示着一个丰收季。














